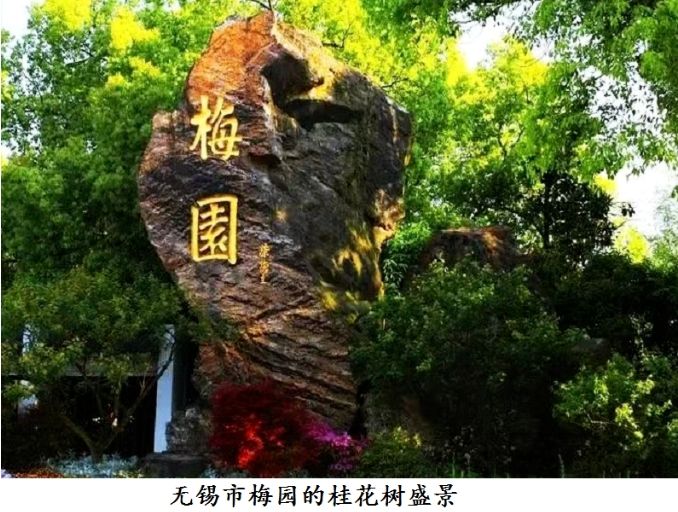酈道元山水文學院簽約作家|夏桐柏
更新時間:2024-09-19 關注:311




夏桐柏 筆名:聽雨,現為中國散文家協會、中國現代作家協會、中國西部散 文學會、荊州市作家協會、中國散文網、國際詩歌網會員;西散南國文學社編委、審核部副主任。2018年入編《中國文藝風采人物辭海》一書。所撰文學作品多散見于《中國散文家》、《上海散文》、《西部散文選刊》并“散文界” 、“西散原創” 、 “齊魯文學” 、“西散南國文學” 、“湖北文學季刊” 、“天津散文” 、“中國散文網” 、“國際詩歌網”等多家雜志紙 刊和文學網絡平臺。曾先后在“李煜文學獎” 、“酈道元山水文學大賽” 、“中國當代散文精選” 、“中國最美游記” 、“中外詩歌散文邀請賽”等全國性征文大賽活動中多次獲獎。有作品入編《中國詩文書畫 家名作金榜集》、《中國當代作家書畫家名作典藏》、《中國當代散文精選300篇》等文集。曾撰寫、導編監利‘98抗洪11集大型文獻紀錄專題片《紀大決戰》和《躍出水鄉的輝煌》等10多部新聞專題 片解說詞并合成。著有散文集《走向遠方》。

邊城情滿沱江流
夏桐柏
相傳天方國(古印度)神鳥“菲尼克斯”每滿五百歲后,即集香木自焚,復又從燃灰中涅槃重生, 鮮麗異常,不再死。此鳥即是我國古代百鳥之王鳳凰。而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湘西古城,自建城之始,即因城西南一山酷似展翅欲飛的鳳凰,故命名之于古城。使得這一風光秀麗的“湘西明珠”,因地靈人杰,獨特的湘西風情,更因鳳凰輩出的名賢代表沈從文先生,以他那筆下流淌出迷人的湘西山水人文情懷,而盛名播享中外。
我知聞鳳凰古城,也是源自于沈從文先生所著《邊城》這一素負盛名的經典之作。沈老在他這篇著力以文字綺繪的一幅幅清麗動人的山水風情畫卷 里,把個山為靈魂,水為血脈的邊城鳳凰(盡管書中描述之地并非鳳凰),把個傲然聳秀,清流奪翠的青黛江山,把個蘊滿神秀風物、情懷獨鐘的神秘 湘西,情天濃濃的情箋于潺潑翠墨,譜出了一曲令后人辭賦不止、贊詠不盡的人文風情史詩。
那是兩年前秋月的一個日子里,我風塵仆仆數百里,驅車來到了古為五溪蠻荒地,今已一朝華麗轉身的鳳凰古城。曾有人說,去湘西,不能不去鳳凰,那里不僅有秀麗的風光和獨特的風情,還有長眠在沱江岸邊的一代文學宗師沈從文先生的一縷文魂賢靈。而我更猶感沈從文先生將山里人原始的淳樸,和自然的人性,用他的精描細琢之筆,升華成充滿了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信念,成就了綺繪湘西風情的獨特一幟。因之瞻懷沈老先生歸泉之棲,成為我夢旅古城的行程之始。
沈老先生的墓地位于古城東郊沱江南岸的聽濤山上,墓地周圍叢林掩映,清幽謐寧。不遠處巖崖底下沱水拍岸,煙云裊裊,浮華流光;秋水浪濤聲應和著山間林濤聲,使得墓冢冥空上濤音錚淙,不絕于耳。睹景思緣,尚記得沈從文先生歷來于盛作中,最是鐘情那“睹目為青山綠水”的湘西風光,甚是向往那“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的田園之畔,更于他多少年來,不管身處何方,耳朵里聽到的依然是那湘西的一濤濤水聲,一嗓嗓拉船調,一號號牛角音,讓他筆下從來就流淌著的故土鄉愁,還有那兒女情長的深深眷戀,總是如那彌漫著湘西情懷而緩緩掠過的河流,唯冀望在春夏秋冬四季輪回的這世外桃源里,盡顯寧靜、安祥、和諧,不再有令身心疲憊的紛爭,不再有曾經縈留身邊的那一絲薄 薄的凄涼……
盈盈沱江岸,秋至風霜繁。褐黃色的落葉蝶飛飄零時,我緩步登臨象征著沈老先生那86年一生艱辛人生路的86級墓道臺階。步近簡樸的墓園, 里面沒有任何形式的墓冢,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墓碑,卻是孤立著一尊據悉從南華山上采下,約有六噸重的天然五彩瑪瑙石而聳矗的石碑,或許這也似在彰顯沈老先生一生奉獻文學,而作出的猶如重徽累盛的鴻彩貢獻吧。先生的骨灰在二十年前葬回聽濤山時,即就將其一半埋在這塊瑪瑙石下,另一半卻是隨著沈夫人張兆和女士于四年時間里,在先生骨灰盒和遺像前奠祭積存的一背簍干枯的玫瑰落花, 一捧捧撒入了滄流不息的古老沱江,讓一瓣瓣還氤氳著的心香,隨著沈老那一縷縷魂髓,戀戀地依蕩著一波波雪浪似的清流,伴著一顆偉士的炳靈悠逸遠去。
兀立墓地的瑪瑙石碑牓正面,鐫刻著沈老先生自書的一生淡泊名利之碑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在碑牓背面,印刻有沈夫人胞妹,時任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的張充和女士撰寫的挽聯:“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碑聯以露尾詩四句中的最后一字結句:“從文讓人”,簡潔精辟的闡釋了沈從文先生生前從來就秉持的謙謙君子之風。
而在離瑪瑙石碑座側后方并不怎么顯眼位置, 還有一塊鐫刻著沈夫人張兆和女士,寫于沈老先生離世七年后出版的《從文家書》“后記”里的一節文字。在這一段節錄刻于碑上的辛酸字句里,充滿著她對丈夫滿滿的愧疚,“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
他。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太晚了!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元好問在《雁丘詞》里曾疑設“問世間情為何物? ”并隨即頓以慨答:“直教人生死相許”。我以為在張兆和女士與沈從文先生的一生情愛間,其最哀莫過于直到她終其一生之際,才恍然開悟苦短人生的幾十年里,即便不能生死相許,又緣何就不能深情相許,一起不離不棄地走過曾經的風雨人生路呢?
沈從文先生曾自述《邊城》一書里的主人公翠翠的藝術形象,就是源自于曾經遇見的“絨線舖的小女孩”、青島嶗山的“一個鄉村女子”和“身邊新婦” 夫人張兆和女士,是以這三個原型合成后塑創出來的。而書中對“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一對眸子清如水晶”的描述,并將女主人 公美以湘西碧翠的篁竹之色而名之為“翠翠”,那筆底下流淌出的清麗形象和美好情愫,正是他濃情刻畫的摯愛夫人“黑牡丹”啊。
先生性格內向、細膩且多情。他愛張兆和,愛的刻骨銘心。他于君子好逑的追慕中,在情天愛河里蜜語漣漣,“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 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此時雖然他們還是師生,但沈從文面對這名令他迷戀得七葷八素的校花級女孩,已然在一封封的情書里,動情地傾吐著“在青山綠水之間,我想牽著你的手,走過這座橋,橋上是綠葉紅 花,橋下是流水人家,橋的那頭是青絲,橋的這頭是白發”那戀侶愛儔間的浪漫蜜語了。
張兆和是民國“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三,她們當時的名氣或可與其同時代的“宋氏三姐妹”齊名。但沈從文看中的并不是名氣,而是不可救藥的愛上了這四姐妹中,乳名“三三”的這一位才高貌美的姑娘。整整四年間,沈從文不間斷寫給張兆和的情書紛飛如雪片,張兆和亦并不為之所動,甚至將他列為夢戀“天鵝”的“青蛙13號”。可沈從文仍固執地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的深情,執著地堅持著即使是“弱水三千,也只取這一瓢飲”的執念。四年里,他等她,等的是肝腸寸斷,一如《邊城》里描述儺送以“孤零地站在山頭上,攢著勁兒唱山歌”的湘西那種特別被稱之為“馬路”歌唱求愛方式,孜孜以求翠翠婚配允諾一般。先生正是因為堅定的明白三三會來,所以也才堅貞不移的癡癡地等待.....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好女也怕纏郎,四年間持之以恒的苦苦追求,沈從文終于等來了張兆和于深情融化后的冰心:“我雖不覺得他可愛,但這一片心腸總是可憐可敬的了”。出身名門望族千金的張兆和此時的應允,只是因為感動,而自認為是紆尊降貴的“下嫁”,骨子里她仍是存著自以為是的高貴意識;而祖上也曾是清廷封疆大臣的寒門才子沈從文,卻還是一如既往地謙卑自詡為“鄉下人”。雖然他抱得了美人歸,卻還是未贏得美人那扇熾愛的情天心扉。
沈從文先生將所有的愛與美都凝聚于“翠翠”一 身,緣以為筆下的她就是自己妻子的化身。天性浪漫的先生,于婚后依然沉溺于文學創作,但甚至在著作等身,名滿中外之時,張兆和也并沒有仰慕于他,卻是蛻變成了一個操勞生活的“油膩女人”,全無了當日的女神氣質。隨著兩人在生活上越來越頻 繁的爭執,已然形成了浪漫志趣與柴米油鹽的對陣,有情飲水飽,于兩人之間成了最大的笑話。在妻子這里得不到情感珍愛和才情敬慕的沈從文先生,終是于不自覺間精神出軌于一名早就仰慕他才氣的文學女青年,先生在這名女子那里似乎得到了一種被認同、被重視的精神上的滿足。他手把手地將這名女孩引入了文壇,卻也為逐漸升溫的情感埋下了危險的種子,不可避免地演繹了一段僅止于凄美的文眷意戀。
先生還是對此時已始萌芽的婚外感情心路,懷揣起了一份忐忑內疚的心情,因為這畢竟有悖于他慕戀張兆和的初心,也有違他致力經典創作的文學理念,他不能陷入被道德譴責的地獄。先生在流言風傳之前即選擇了向妻子坦承心跡,釋其精神出軌的初衷,只是為求顯示自身魅力的砝碼,只是希冀喚醒他的三三給予他期望的情感回應,以乞得到妻子從未給予的理解和認同。誰知他的“坦白”卻是換來了相反的走向,清高的妻子不僅沒有理解丈夫冒大不韙“出軌”的意圖真相,遽然間,卻更加激起了原就十分優秀的她,頓時難以抑制中燒起的怒火, 最終憤恨且傷心、痛苦地回了娘家,開啟了他們長達四十余年的分居生活。即使后來也有過短暫的聚合,終因張兆和認定丈夫是“忘恩負義”,并及各種因素而沒能諒解丈夫。然而即便是在浩劫中潦倒窘困的日子里,即便面對“莫須有”的橫加指責,面對惡意構毀之令人發指的焚稿高壓, 先生都能漠然置之;可在面對妻子長時期的冷漠和決絕,先生卻仍于咬緊牙關中,始終無悔地依依尋求著他衷愛的妻子的諒解。
先生又開始給妻子寫信聯系了。他有時欣喜地像一個老小孩樣,喜極而泣的和親友分享偶爾收到妻子難得回信的興奮,他可是癡心殷盼地等待了他 的三三大半生啊。而張兆和此時間卻仍是放不下心魔,她在徒使沈老先生于心酸中繼續與孤獨清冷相伴的同時,也在仍然延續著自己備受煎熬的痛楚日子。她在婚姻中的清高與冷漠,障礙了兩人一生本應甜蜜的幸福生活。
沈從文先生將魂牽夢縈對妻子的思念,都融進 了一如《邊城》里的翠翠,《三三》里的三三,《長河》里的夭夭等這些他由心底里構思的美好人物塑造中。地老天荒,此情不泯。先生此生給他的三三累寫了難以計數的如“我喜歡你,像風走了八萬里,不問歸期”這樣柔情戚戚的情書,這樣的愛情雖然卑微,卻也愛得深沉,愛得濃烈!就是在沈老先生彌留之際,他拉著妻子的手,說的最后一句遺言仍是歉疚的心聲:“三三,我對不起你”!如果不是深愛,有人能在咽下最后一口氣前,還會將幾十年間未有放棄的自責看得如此深重嗎?問世間又有幾多男子能做到燃情如此?能做到如此專情專守幾十年而無怨無悔呢……
他一生都在等,等他的三三融化她心中堅封的冰雪的那一天,等他的三三終能像他筆下《邊城》的翠翠那樣,俏然地把他像“心上人儺送”那樣放在心尖最柔軟的地方,靜靜地守候在那盡歷人生風雨的渡船上,固執地等著他登船蕩槳,攜手并肩劃向風雨人生最后的彼岸……這一天,沈從文先生 終于等來了。動亂過后,也已是步入晚年的張兆和女士,帶著對丈夫難得的理解與寬容,帶著對丈夫幾十年不懈堅持的堅守與對自己心靈的沖擊,她的那一絲柔軟終于蕩開了浸擾她幾十年的心魔,回到了沈老先生的身邊,慢慢開始了與丈夫享受最后只剩十年的甜蜜婚姻生活,偕伴先生幸福地走完了遲到的黃昏戀之心路。直至十年后,張兆和女士終致日夜痛楚地守護著病榻上那個一直將自己作為女神 和精神支柱,此際行將油枯燈盡的先生,癡癡地看著他在他標志性的溫和笑容中,安祥地溘然長逝。
“作為作家,只要有一本傳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了。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從爛紙堆里翻出他越多的遺作,哪怕是零散的,有頭無尾的,有尾無 頭的,就越覺斯人可貴。”這是張兆和在沈從文先生身后,為之整理《從文家書》遺稿時,情動憾書 “后記”中的一段文字。唯只嘆直至當兩人已然陰陽相隔之后,張兆和才驀然有了擊節贊賞夫君在文學上極具天才造詣的欽佩貞情;才俯然有了對夫君來自三個民族之后的“貴胄”家庭,卻始終謙稱“鄉下人”的敬佩衷情;才嘅然頓悟夫君幾十年堅守慕戀不變,并將自己在他筆端下化為心中女神的感佩閨情;才劇然理解了夫君幾十年孤苦間不改初衷,屈辱間不移風志的景佩高情。然而等到醒悟終知遲, 外頭的人再怎么長嘆,里頭的魂靈卻是再已無從回 應了。
我佇望聽濤山,凝聆沱水聲,透越霜嵐煙,這湘西蹻蹻青山雖荒僻崢嶸,卻因原始純真、蒼秀豐厚,而翠微秀映著鳳凰古今煙火人家。這千年漭漭沱江雖無黃河長江的恢弘壯闊,卻也以源遠流長、清瀅秀澈的泱泱水流,潤澤了一代文學宗師的椽筆之毫,才有了沈從文先生筆下譜出的那百年絕唱的湘西山水風情華章。那倒影在沱江水里的吊腳樓, 清鏡里蕩漾的是驕具民族風韻的窈窕身姿;孤零孑立于水中支撐吊腳樓的伶仃木柱,托起的應是邊城一段艱辛沉重的歷史;而那吊腳樓頂一栩栩展翅欲飛的翹檐鳳凰,恰是古城人民自古就傳承敬奉的一片千秋心念。
兀立于北門城樓下沱江水中的一列石墩跳巖, 還在久遠的年代里就一直是古城人出走山外,回歸故鄉的主要通道。它承載著鳳凰人胸懷天下,走出古城,走出湘西,走進山外世界的豪情壯志。沈從文先生或也是從這列跳巖上,以湘西青山為脊梁, 以沱沅酉水為血脈,以武溪清流滋育的那份湘西情懷,走向了他畢生為之嘔心瀝血唱響湘西、書頌祖國的文學創作之路。
正如先生孫女沈紅奠書在故居里的祭文中寫 道:七十年前,爺爺沿著一條沅水走出山外,走進那所無法畢業的人生學校,讀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 大書。……他也寫了許多未必都能懂的小書和大書,里面有許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畫卷,這些文字與畫,托舉的永遠是沅水邊形成的理想或夢想。”
沈從文先生以這種在湘西山水間就懷揣起希望的理想,將他豐富的愛祖國、愛人民、愛故鄉的一泓深摯之情,柔懷且不失堅毅地,用畢生心血凝成 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豐碑,站成了迄今為止一代代成長中的學子們仰崇的文學宗師,書下了古城鳳凰里一抹永恒輝熠的人文風景。
和煦的秋陽正灑滿了這座江南百年四合院的天井庭院,一批批從遠方慕名前來參謁的人們,不僅僅只限于沉醉在鳳凰的旖旎風光里,他們更悅心親瞻沈老先生故居里各種紀念珍品的風韻,更喜沈老先生那筆端百流匯成滄海的滔滔妙句華章,將一摞摞清華的文化泉源引流四方,從而滋潤起一個又一個溢彩流光的春天。

-
上一篇:酈道元山水文學院簽約作家|楊七七
-
下一篇:酈道元山水文學院簽約作家|李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