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界晨報】高喬明 | 姐夫
更新時間:2024-11-02 關注:123

龍年的清明節即將到來。近日,身在海口市南國威尼斯城的我常常夢見已經逝世六年多的姐夫劉忠豪,一幕幕往事就像發生在昨天一樣,浮現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見到姐夫,是1972年的冬天。當時,他從河南明港的8231部隊回家探親,借機到我家“上門”提親。聽父母講,兩家是老親戚,俗稱“卷卷親”。

姐夫劉忠豪參軍遺照
他約一米七的個子,著一身綠色軍裝,略顯黝黑的國字型臉龐,在鮮紅的帽徽、領章映襯下,顯得莊重威武,且有些拘謹。禮物是給我們族親三家,分別送了一包黃麻紙打成斧頭狀的蔗糖;另外,特地給我送了一支紅色的鋼筆。這支夢寐以求的鋼筆,使我對姐夫一下子少了許多陌生感。當天,我如獲至寶,反復把玩,不時蘸著白水在手心試著寫字,舍不得啟用;晚上,用手帕包好后,讓母親藏在枕頭套子里。可是,第二天中午,當我放學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擬拿鋼筆欣賞時,翻遍枕頭也找不到。原來,姐夫還有一家親戚要去,卻沒有準備禮物,母親便臨時將鋼筆拿給姐夫“應急”了。我一聽,急得大哭,關起房門不吃飯,硬是鬧著要母親去討回那只鋼筆。但這也是覆水難收的事情。姐夫見狀,好像自己做錯了事,一時手足無措,滿臉窘得通紅,有些語塞地說:“再勒(那)個,再勒個!”過了幾天,他在歸隊前,不知從哪里弄的錢,買了一支同樣的鋼筆“還”給了我。回想那時我才9歲,真是少不更事。
姐夫為人像他的名字一樣忠厚本分,能吃苦,有擔當,肯上進。他于1968年4月應征入伍,由于學習訓練刻苦,軍事技能過硬,擔任炮長,1971年3月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左手在訓練時負傷,于1973年2月退伍回鄉,當時部隊一次性給予傷殘補貼45元。后來,手指經常發麻發痛,干活不得力,但他從來無怨無悔,總是以自己曾經是一名共和國的軍人為此生最大的榮耀。
他與我姐是1973年“五·一”完婚的,第二年春喜得長子。當時,祖孫三代十幾口蝸居在三間的老房里共同生活,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后來,兄弟們分家,單起爐灶,小家庭的日子捉襟見肘。這時,還突然發生了一件令人心碎、不堪回首的慘事:不滿一歲的次子因無人照看爬到糞窖里溺亡。姐夫和姐姐痛不欲生,遭受了人生最為慘烈的精神打擊。1976年,姐夫被云夢棉紡廠招用為臨時鍋爐工,每月工資45元,除上交生產隊20元買工分外,其余可貼補一下家用。鍋爐工上班實行“三班倒”,工作環境臟亂差,且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許多工友因吃不消這般苦而不辭而別。但為了全家的生計,姐夫每天起早貪黑,風雨無阻,涉河渡水步行往返30多華里上、下班,一干就是漫長的六個春秋。
1978年后,姐夫的女兒和小兒子相繼出生,家庭的負擔日益沉重。為了闖條生路,姐夫與我哥一起,在縣城南郊的街道開過小餐館,不久因客源少、賒賬多而關門,東挪西湊來的千把元本錢,最終變成一堆破鍋爛盆。繼而,他年近半百又加入建筑大軍,背井離鄉闖東北,頂風冒雪干了幾年小工,終是賺不到什么錢。這些年吃了多少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古人云:“一個女婿半個兒。”在左鄰右舍看來,姐夫卻是“個半兒”。我們兩家同處一村,分屬三隊與五隊,房屋相距僅百步之遙。我的父親是個“藥罐子”,長年病魔纏身。1977年冬,我哥參軍,一去八年多。我年少尚不得力,1984年秋也離家求學去了。于是,姐夫成了我家的“頂梁柱”,除了每月定時從城關中心糧店買運回全家的供應糧之外,日常擔吃水、挑水糞、出豬欄糞和耕種自留地等苦臟累活,幾乎統統由姐夫包攬下來,但從來沒有聽到他叫過一聲苦,喊過一聲累。

姐夫(左)、姐姐(右)和兩個孩子合影
在我的記憶里,姐夫對于我像親哥哥一樣實心。記得我考取師范,即將前往學校報到,卻沒有行李箱,無奈之下,打算用兩條蛇皮化肥袋子湊合一下。姐夫見狀,覺得這樣太寒磣,怕我被同學們瞧不起,便不聲不響弄來一口淡藍色的漆木箱。這口木箱大小適中,做工精致,結實耐用。后來才聽說,是姐夫找熟人花了10余元錢買來的。次日早晨,侄兒新文幫我挑著木箱,送我告別父母和家鄉,踏上了人生嶄新的旅途。這口裝滿愛和希望的普通木箱,伴隨了我好多年,每當看到它,就像看到姐夫那親切的面容。
姐夫是個大孝子,也是個大孝婿。他嘴拙,從來不講“熱”人的話,更不會“哄”人。對我的父母,因是“老親戚”,從小叫慣了“四叔”、“嬸媽”的緣故,一直沒有改口隨我們喊一聲“幺爺”和“媽”。但是,他用默默無聞的實際行動,詮釋著什么是孝心。幾十年里,我的父親每次重病,他總是日夜守在跟前,伺候湯藥,端屎倒尿,無微不至,任勞任怨,令我這個做兒子的自愧弗如。
記得父親晚年,曾特地跟我講過一件事:前幾日,父親便秘10多天,吃了各種瀉藥也拉不出來,肚子鼓脹得厲害,痛苦不堪,被送到城關醫院治療,大夫及時灌腸,仍不見效。無奈之下,姐夫便讓父親趴在床上張開雙腿,撅起屁股,他貓腰半跪在床,雙眼湊近屁股,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扒開肛門,足足花了小半天功夫,才用棉簽將一截堅硬如石的大便,一點一點地掏了出來,令在場的大夫和護士深受感動。父親滿面幸福地叮囑我道:“你這個姐夫雖說拙口笨腮,卻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你們日后千萬不能馬虎他哈!”不久,我見到姐夫向他道了聲辛苦,哪知他卻急忙揚手打斷我的話,顯得有些生氣地跟我急起來:“哎呦,盡說些傻話,勒個——勒個——是我應該勒個的!” 過了一年多,父親去世了。父親的話,竟成了他惟一的遺囑,常常在我耳畔回響。然而,造化弄人,一向看起來身體硬朗的姐夫,也患了不治之癥——肺癌!

姐夫(右)和姐姐(左)生前留影
面對絕癥,姐夫積極配合治療,顯得堅強而又淡定。最讓我心碎的一幕是,2017年深秋,我的侄媳望秀去世,姐夫不聽勸阻,強拖著病體,堅持回老家送望秀最后一程。在下葬現場,我看到姐夫形容枯槁,黯淡無神的雙眼含著淚水,既飽含著對親人去世的悲哀,也充滿著自己對生命的渴望。我緊緊地依偎在他的身旁,不知道說些什么為好,耳邊想起《葬花吟》中“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催人淚下的詩句。那一刻,我倆其實心里都明白,這是病人臨死送故人,真的好殘忍!大約過了兩個月,姐夫也走了,享年67歲。我不禁疑問,難道真的是好人命不長嗎?此生,我又怎么遵父親所囑——“不馬虎”我這“拙口笨腮”的姐夫呢?每念及此,我就心痛不已,惟有用綿綿不絕的思念來報答姐夫。
姐夫和我姐姐相濡以沫,攜手走過了45個春秋。令人欣喜的是,如今,年過古稀的姐姐,身體仍然康健。他們的三個子女皆忠厚本分,工作踏實,各自的小家庭和和美美,日子過得平靜而巴適。孫輩四個已有兩人學有所成,參加了工作。
古人云:“忠厚傳家久”,看來,此言的確不虛。我想,如果姐夫九泉有知,一定會倍感欣慰!
作 者 簡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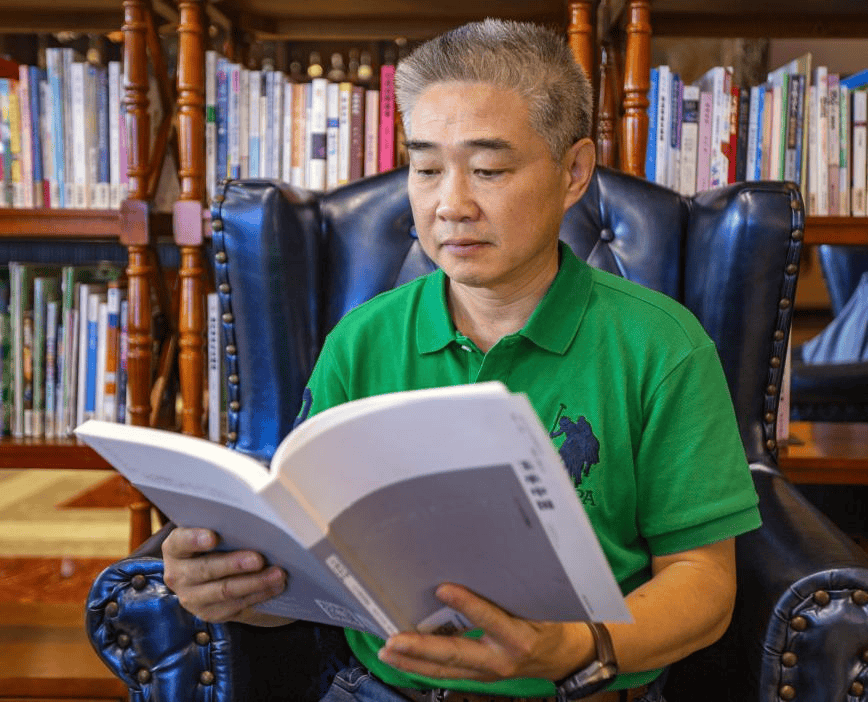
高喬明,男,漢族,筆名下里蒿人,1963年5月出生,湖北省云夢縣清明河鄉人,中共黨員,正縣級干部。歷任民辦教師,縣直機關股(科)長,鄉鎮黨政主職,縣委、縣政府班子成員,省直機關副處長(掛職),市直(地級)機關領導班子成員和主職。現為孝感市作家協會會員,業余時有詩歌、散文見諸報刊和網絡。2022年10月,由中國人文出版社出版詩、文選集《飛鴻雪泥》。
(中媒文化融媒體中心)
-
上一篇: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