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中國當代實力派優秀作家 王志嬌
更新時間:2024-09-19 關注: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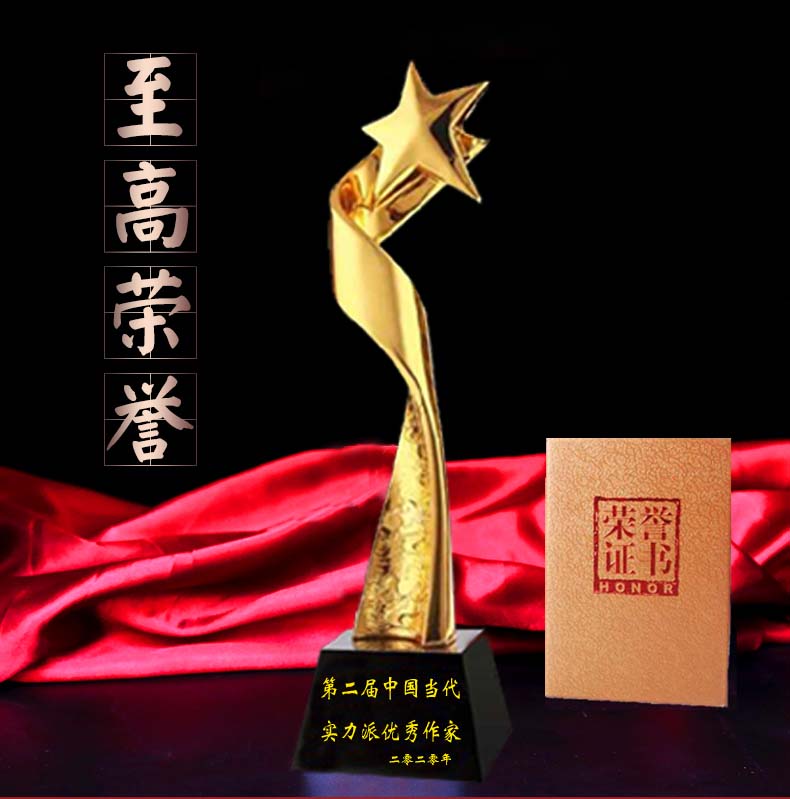

王志嬌,筆名男孩兒,90后女孩,語言學在讀碩士,作品《我與父親談了場戀愛》《生命告白》《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致再見·前任》《愛像風箏斷了線》和論文等散見于國家級報刊雜志及文學網站。
作品賞析
世界予我的第八個清晨
文/王志嬌
我喜歡牽著父親的手在路上行走,太陽愛我,他也愛我。
我也渴望成為一片大陸,在他的注視下,手捧著,一簇鳥語,兩盞花香,大搖大擺地,穿梭于茫茫花的海洋。
我喜歡騎在父親的脖子上,在云間穿梭,一邊牽著虞夢,一邊曳著雨滴,一面暢游未來,一面滋潤父親種下的希望。
我也渴望化作一朵胸前的黎明,披著粉紅色的外衣,在父親的寵愛下,接受黑夜,迎接輝煌。
我時常赤足于時間的河流之中,享受時光從腳趾縫間川流不息的即視質感,偶爾向著河岸那畔的父親遙遙相望,這再熟悉不過的舊世紀豐碑,正是世界贈之予我的第八個清晨。
小時候,讀不懂顧城的詩,更讀不懂父親為什么總是起早。
以往的歲月靜好,常常是還未拂曉,即被父親叫醒,然后心甘情愿地從暖暖的被窩中爬起,默默地感受著父親起早的完整經過。哦,原來父親就是這樣每日追趕月亮的!
自古以來,北方的冬夜渾身是雪,那雪堆砌得整整齊齊,都延續在父親棕褐色的鐵鍬上,一锨一鍬,上升下落,就著古老而傳統的掃帚有節奏地在半空中揮舞,繼而伴著一條條清晰而寧靜的雪道,自南至北,由東延西,似乎正在等侯遠方重要的來客,又像是于平日里在大地之上彈琴種花的消遣,那吱呦吱呦的“琴聲”猶如仙境里的天籟,“應是天仙狂醉,亂揉碎了白云”,日出皓兮的雞鳴,是心之所善,亦是余襟浪浪。日里的雪仿佛是陪伴在孤獨父親身旁的白月光,她那么近,那么靜,和寡言的父親一樣,果不其然,真正的愛又怎能輕易掂出它的沉甸?
轉而,我牽制住內心飛絮的思路,這才聽到了父親按下水閘的聲音,踩著廚房里不絕如縷的切菜聲,嘩啦嘩啦,可喜,可愕,可歌,可泣。
這熟悉的一幕,串著酸甜苦辣的光陰與生命拔節的繁華,竟在我不大不小的記憶長廊間殘存了十幾年之久,如今不經意間摸起那本泛黃的日記,卻恍若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的光景。小時候的腦海內缺失了嘰嘰喳喳的玩鬧,卻偏偏絲毫不覺晦澀,猶如我和父親之間的愛,終歸是經得起歲月的彈劾,沉默間發出陣陣迷人的聲響。
春末夏初起早挑瓜,是我對清晨與父親的又一抹記憶。
我自幼“遺傳”母親,最愛吃瓜。于是,每逢暮春之際,父親便早早地駕著那輛村里最耀眼的摩托車,帶我去升陽的瓜地里買瓜。
我不知道父親為何偏偏挑中早晨的時間前去那么遠的地方買瓜?或許是因為他怕耽誤上工?還是清晨的瓜最為香甜?亦或是單純地為了讓我跟著起早?
父親是個粗心的父親,但對要帶回家的“寶貝”可謂是精挑細選,目光所及時而像丘比特的愛神選箭,時而像挑選荔枝的醉酒楊貴妃。父親對錢之類的俗物向來粗手粗腳,自是對瓜的價格不拘小節。他時常一邊選一邊叨嘮:“選瓜如選人,重在看心、看品質,看他內心的缺失,正是從這瓜秧下的根得來。”
母親聽了,便不解風情地調侃到:“這樣說,以后你得親自為女兒挑中個好女婿呢。”
父親停住了掰瓜的手,一屁股坐在自家庭院葡萄架下不到半米高的板凳上,“女兒是八九點鐘的太陽,她的世界大著嘞。她的事情她自己做主,當父母的,相信她,索性就讓她放開手腳去闖。”
我雖表面上若無其事,心里卻對父親一副高風亮節、成竹在胸的模樣嗤之以鼻。“做父親的,當真不怕女兒被騙?不怕我抓個大逆不道的“地痞野獸”回來,丟人現眼不成?”
買瓜回來的路上,太陽的腰已經抻起老高,我坐在父親摩托車的后蓋上,一時間很是惱苦,為什么視線之內僅夾著整箱零一袋的瓜,而我卻冥冥覺得,自己與父親的距離好遠好遠。我總是害怕“不愛我”的父親,要瓜不要我;后來長大一點,依舊擔驚受怕,生怕粗枝大葉的父親丟了我,也丟了瓜。
因為起早買瓜一事,我沒少向母親告狀。今天狀告父親半路把瓜摔了,明天或許就是為了趕工忙,開了快車的說辭,總之有母親撐腰,我便可以理直氣壯地“為所欲為”。縱然我說什么,父親依舊沉默不語,可越是這樣,越引得母親發笑,前仰后翻間當眾指責父親,不會照顧孩子,說是再也不要我跟著父親起早了。我聽了,當時便直覺得晴天霹靂,“為什么小聰明一世,卻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家的腳?”
其實,父親雖然表面上不言語半字,卻總是偷偷地向母親稟告我的進步,“不用擔心了,勤奮著呢,看瓜的眼光精準不少呢,還會討價還價,總幫我跟人家老李講價,省下不少錢都被她給私吞了。”
“眼神也好,瓜農老李一股勁兒地總‘夸’她,說是讓我買瓜自己來,千萬別帶‘老佛爺’。”
“小佛爺咋又來了,你別來了,買瓜不講行情。到我地里來,大瓜,好瓜凈你挑,還得折扣好幾毛錢,以后得嫁到我們家來當童養媳,不然你爸的瓜,我老李貴賤不賣!”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搬出“祖傳”的看家本領徹底和他杠上。關于彼時耍乖賣寶的斑斕記憶如今早已模糊不清,只見得那時的日記仿佛格外豐盈而晴朗:
“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都習慣清晨。”
老李一邊哈哈大笑,一邊給父親點煙,嘴上不停地夸我既機靈又勤奮,小小年紀就能起大早,跟著爸爸跑出大老遠的地方選瓜。“自古得天下美瓜而盡妻之,瓜都這樣大,到底是要帶走哪一個才好呢?”
多少次臨走之時,老李盯著衣兜里被我順走的瓜,生要把我從父親的摩托車上拽下來,我嚇得大哭,大吵大鬧之際,這才和賣瓜老李結下了死敵。
以后的以后,每一次選瓜,我都早早地爬上父親的摩托車。任誰生拉硬拽,死也不放手,導致現在每逢夏季捧瓜的時候,我都情不自禁地對仇人老李思念有加,想知道他現在身體怎么樣,還兇不兇,摳門不摳門。
現在的我,也正努力地學著跟父親一樣起早,學著和他一樣,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一樣地追著夜晚的月亮四處逃跑,但卻唯獨沒了父親拉著長長的大門的聲音和開閘放水的自然回響。印象中,父親獨自吃著自己做的早餐,咂米粥的聲音騷動著我們快快起床,現下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讓越來越多的人晚睡晚起,她們錯失了一日之計里多少個美好的開始,又在多少個夜里孤影自憐地收拾著現實摔在地上的邋遢而過去的碎影,然后日夜兼程,重蹈覆轍。我亦飄零久,清醒的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走了那么遠 /我們去尋找一盞燈 /你說 /它就在大海旁邊 /像金桔那么美麗 /所有喜歡它的孩子/都將在早晨長大
自古黎明與清晨之間時有交叉,從凌晨到拂曉,從拂曉邁向黎明,第一次覺得時光可以這樣清晰,這樣慢而滿,這樣美,這樣奧妙,這樣舉世無雙。粗茶淡飯的日日打磨下,父親的清晨就著柴,柴就著油鹽醬醋,一齊穿越布滿皺紋的煙囪,化作永恒記憶里人間煙火的古老塵味,令人再熟悉不過。多么希望起早的人能多一點點,以此,人生的遺憾也就減少一半。
未來的路上,我還要結識好多好多的人,和好多好多的事。父親的早起不是熱情,更無關勤奮,不過是年深月久,早已凝做愛的禮物,成為了我和母親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彌足珍貴地鐫刻在手掌的生命線,懷念,抑或尋找,來日方長,時間,會讓強烈的東西愈加深刻。
未來的日子里,我還要遇見好多好多個清晨,過去是我的,那屬于我的未來,也定只有獨一個。我會未來著每一天的未來,讀城市衰落,盼日出復活,看春江晚景,送秋景蕭疏,我愿換裝成海上的大魚,和勇敢的海棠一起,懷著感恩的新奇探知人類世界的另一個海底。我多么希望,有一個永遠到不了清晨的清晨,一晌夢,一陣風,我只用指尖,觸了觸陽光,醒來時和父親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
“流浪”孩子與牧羊犬
文/王志嬌
“誰家庭院自成春,窗有莓苔案有塵。偏是關心鄰舍犬,隔墻猶吠折花人。”這是父親讀給他的最后一篇打油詩。突如其來的車禍,使男孩失去了唯一的至親,他17歲,一貧如洗的小家卻還是依然富有,富有到唯獨擁有一只牧羊犬。
這兒遠離鬧市區的喧囂,黛色的瓦墻,泥砌的柵欄,還有大片大片的芳草地,恍若城堡中的莊園,夢幻而古典,那是一種羅切斯特式不摻雜質的美,男孩微倚著體格健碩的德國黑貝,眼神之中似有偏離惆悵與等待的失落。牧羊犬一月之多,笑不露齒,似乎胸有成竹,訓練有素,黝黑發亮的臉龐、厚毛、豎耳、杏眼,搭配結實有力的肌肉,鋒利的四爪似是有意隱藏著內心的沉重與兇猛。若近瞧,其肩脊筆直,背披黑灰,腹埋咖啡豆一般的棕黃;若遠望,則各部位和諧而勻稱,端莊而高雅,勝于剛柔并濟,卻絲毫不似盛氣凌人。此時,它正依偎在主人面前,風情萬種地咀嚼著咬膠,那磨牙聲柔柔細細,流淌在唇齒間似點露著絳珠仙草的萬般愁情,周圍散落著的,是幾枚干燥的狗糧和十多張帶著父親筆漬的生日賀卡,另一旁,松脆的干肉餅悄悄地學著牧羊犬的模樣,頤指氣使地賴在草地上曬太陽,暖風定然吹不走,這聰慧,這忠誠,這一臉憨態,這甘愿臣服......
“黑貝,你會唱生日歌嗎?記得每年,父親和你都會一起給我過生日,我很想他......”哽噎的話音遮擋了前來報道的烏云,沉沉的天空似乎一秒間恢復了往昔的光亮。
“現在家徒四壁,我窮寒得只剩下你了,但......是不是也算一種幸福呢!”說著,黑貝悠哉游哉地竄進了男孩的胸膛,托著一臉的篤定與沉醉,迎上獻吻。
“在家要照顧好自己,要吃飽,要睡足,好嗎?......”我會讓楊奶奶來看你,人類中,你只可以相信她。”男孩轉身上車,留下了一路追著跑的黑貝和狼藉滿地的思念。
這是他們第一次分開,高二的男孩總要獨自背著書包去偏遠的郊外求學。除去規定節假日,一個學期只能回家一次。
彼時,白日西沉,曲曲折折的回憶深處,是流年雕刻的印影與父親講過的數不勝數的狼犬故事,對比而今現實冷清,也唯有黑貝能夠在貧瘠的歲月里散發出永恒的光鮮與魅力,抑或是在遙不可及的黑暗中熠熠生輝。可每每想起英年早逝的父親,那暗無天日的團團陰霾,那并肩作響的灼燒與疼痛,使他再也不敢過馬路,不敢看車來車往,不敢想川流不息,不敢深信不疑,更不敢全然依賴。后來,慢慢地,竟是黑貝陪他成長,左右庇護,直至他戰勝恐懼,重啟希望。自此,即使是為了黑貝,那雙童真的眼睛也斷然不會輕易落淚。
曾幾何時,他學著父親寫蘸掛深情的文字,那由瑣碎拼湊而成的厚日記恰如舊約圣經里的諾亞方舟,載滿了歲月悠悠和“流浪”男孩與牧羊犬的點點滴滴:
“今日午后,我們外出散步,誰知,于冷血的旁人而言,黑貝居然成了‘窮兇極惡’的敵人,無辜地被定下了‘恐嚇’嬰兒的罪名,莫須有的威脅一度令我陷入了兩難境地,這時,又是黑貝拯救了我,它主動地趴在地上認錯。我也只好配合著‘狠狠’打它。由輕到重,再由重到輕,靈巧的“笏板”在來自寬恕之情的半空中來回揮舞,羞愧的淚水促成了模糊視線的橫流,豈不知,它凌厲冰霜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實是出于對弱小的我的保護,這一點,我又怎能不知不懂?”
“我時常渴望成為低空中游散的云彩,沒有悲歡,亦不必焦躁,然后任性地,隨你遠行,帶你馳騁。”
“又或者我是你,代替你受傷,像你陪伴我一樣,從來不曾孤單過。”
誠然,從冷酷兇殘的亞洲狼被馴化至今,割舍之途可謂漫長而艱苦,歷史荒蕪的硝煙重重,狗無疑脫離了祖先的群居天性而成為了宇宙孤獨至極的存在——沒有親人,沒有伴侶,沒有后輩與自由,更沒有除主人以外的任何朋友,在人類眼球中那纏繞得千絲萬縷的七情六欲,在犬類尤為短暫的生命線中竟空白得如此可憐,有聲的世界里,吠聲自然而然地成了它們唯一的語言......
每一次楊奶奶打來電話,男孩都能聽到熟悉的聲音,那牽動人心的想念,沿著長長的老式電話線放浪翻滾,而后便在稀薄與艱巨的兩極間勾留輾轉,同頻共振。
冬去春來的光陰,若白駒過隙,倏然而已。男孩邁入高三,模糊不清的未來遙遠而笨重,內心對黑貝的惦念與愧疚自是愈發響烈。多少次煙雨茫茫,東風懷愁,他都想起那個永遠走在自己前面的黑貝,那個支持他、并永不悲傷地走向遠方的牧羊犬。 百感交集之際,他又欲說還休,只得死死地攥緊了手中的筆,口不絕吟地,投入到了新一輪的戰斗當中。
冥冥中,卻不知為何,男孩似乎預感到一股呼吸聲正由遠及近,帶著些許急張拘諸的氣勢,朝自己這邊的磁場席卷奔來。
“是黑貝?”
“不!不會,這么遠,黑貝也早已不再年輕......”男孩立馬否定。
“只是......這聲音愈近愈像,竟還自動踢踏著生日歌的節奏”。男孩猛然掰開隱匿在校服袖子里的手表——“不偏不倚”,今天正是見證他駐足人間18年的生日!
“黑貝記得!它......是特地趕來給我過生日的!”
牽扯著慌張的思緒,男孩箭一般地沖出教室,見到黑貝的那一刻,男孩激動得涕淚滂沱。在青草還未蔥郁的操場上,他隆重地舉行了自己的成人儀式。
他目不轉睛地看著眼前的黑貝,想它曾也一身英俊、兩方“梟雄”,如今老之將至,睿智的眼神卻愈顯清透。只見它慢悠悠地扭過去,憨態可掬的笑容中浸滿了得意的歡喜。春風拎笑,吹過它黑黢黢的鼻毛,那掠過驕傲的唇和略帶蒼老的剪刀狀咬齒于無形之中毅然擰成一種默契的過渡。曾經通體和諧、體毛直硬,如今密布在外,延展不一;曾經后腿富毛、前腿徑直,如今鐵漢垂暮,分外有力卻也幾度滄桑,瀟灑多姿卻也敏捷有度。微微上翹的尾巴流溢著凹凸起伏的彎曲,在百花爭艷的春日仍舊可圈可點。包裹的人群縫隙里,只窺見一條毫無褶皺的舒展弧線從耳尖途經背部抵達至此,悠悠晃晃,時隱時現。它將含著的生日五彩燈立放在男孩的腳邊,伸長脖子,輕輕地搭落在主人的雙肩,后將其深擁入懷,那原本緊密的腳趾間,似呈半圓狀的拱型,卻碾磨著長途跋涉的磨損。想必,此間所有不緊不慢的溫存,定會從日后許許多多的夜幕中尋得一個看似平凡的角落,然后默默陪伴,堅堅挺挺,然后長相廝守,戰勝、倔強。
假以時日,犬日將盡,鼻息無存,它便幻化成一顆牧羊星,鐫刻在主人的心頭。所以,男孩也并不空空如也,而是牽著與牧羊犬的回憶,在黑夜盡頭踽踽獨行。縱然一路流浪也常有傷痕,但內心積攢感動的小河,怕是一輩子都刻骨銘心。所謂生命,大概是一次又一次送別,黑貝縱然是他的青春,他又何嘗不是黑貝的整個世界?
試問黑貝:為何你的眼里常含淚水,是對這“世界”愛得深沉?






